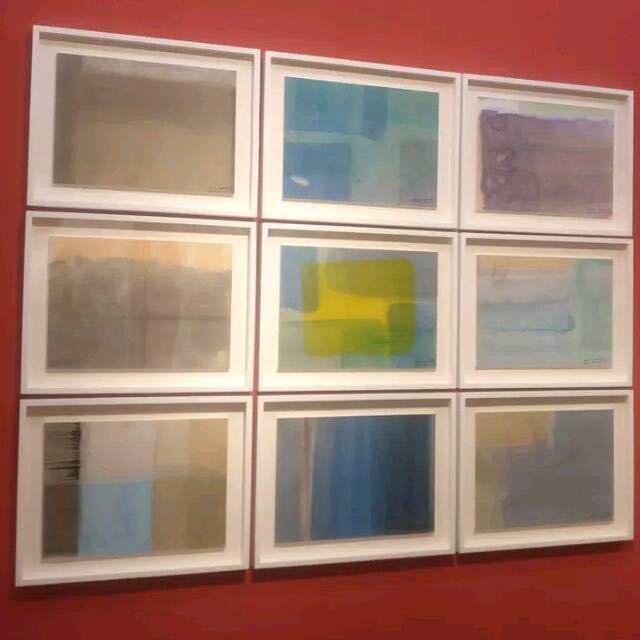如果这篇博文对您有所帮助,您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
CC-BY-NC-ND 4.0(除特别声明或转载文章外)
在文章开头随便写写的话
莫泊桑凭他的那份伟大,把写作水准提得那么高,弄得人很难下笔,可是我们仍旧得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在写作方面得有勇气才行。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懒。大狗和小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好了。
在拿到港中文社会学系的PhD offer以后,我在朋友圈写下了“整理一下心情,过两天写一篇申请的总结”这句话;它毫无疑问地又成为了我一个立起来的flag,得益于我的拖延症,这篇本来应该在二月份写好的文章就一直到了四月下旬才开始正式动笔。
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有点吹毛求疵、过分关注细节的人,这让我规避了一些积于忽微的问题,但也让我产生了严重的拖延现象,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从今年八月开始正式地改掉自己的拖延症。
既然是申请的总结,那么就不可避免的要按照某种泛用的格式去完成本文的一些内容,这里部分参考了知乎问题“2021 fall你都申请了哪些学校的MS/PhD?录取结果如何?”下的一般格式。
基本信息
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辅修政治学与行政学,主修辅修GPA都是3.6/4,雅思7.5,申请时是港科的大数据技术硕士在读。和大多数目标明确的朋友不一样,其实我在去年8月以前完全没想过读博的事情,更不用说是社科的博士了。
科研经历
社科相关领域的科研经历到申请时也才不到半年,在此之前流浪过两个CS的实验室,没有任何publication。从数量上说我是勉强凑够了推荐信,不过,推荐信的力度应该是可以的。
选校
HKUST MPhil in Social Science, CUHK PhD in Sociology
其实谈不上什么选校,北美的社科PhD的训练时间太长了,我想早点毕业,所以只申请了香港的两所高校(貌似港科上一次直接发放PhD的offer是多年以前了,所以只申请了MPhil)。而至于只申请两所高校,一是因为当时盲目自信,二是觉得自己申请失败的话,去工作也不错。
其实现在回头看也许应该再冲刺几所美国的学校的。
录取结果
HKUST这边我面试表现不太好,只拿到了CUHK的offer。
经历
下面是一些申请过程中的经历。
HKUST
与很多理工科项目只要老板点头同意就能拿到offer不同,社科这边录取委员会对最终录取结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很不巧的是今年我在两所学校的两位意向导师都不在录取委员会里。
先是提交了港科的申请、参加了港科的面试,说实话面试表现很不怎么样。
面试糟糕的原因很简单,我准备面试的方向完全反了:在计算机系,面试官会详细地问你过去的项目经历,而在社科领域,你会被详细地询问你的研究计划书中的细节。
于是,面完的时候我就在考虑第二天要不要去刷Leetcode了。
CUHK
刷了两天的Leetcode之后,打算还是调整心态准备面试、走完CUHK的申请流程。
我原本是将港中文的项目当作一个备选项的(觉得总是至少要申请两个学校的),套瓷完导师以后我甚至都没发follow-up的邮件;一月二十九日截止材料递交,我一月二十八日把材料递到了系里,随后在二月二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二月九日的面试。
而那时候我甚至连推荐信都没交,实际上,我的两封推荐信应该是分别在面试前一天和面试结束的那一天交的。
感谢套瓷的导师帮我做的mock interview,加上HKUST给我的教训,这次面试我没出大岔子。随后在面试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十日早上,我收到了录取通知。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申请季。
一些想法和故事
作为一个outlier,我的经历也许没有什么参考性,如果说有什么我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我想说的主要是下面的这些(以下均为暴论)。
“没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GPA、发表经历、本科硕士背景、专业匹配度,这些很多时候被用来衡量录取可能性的话题,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 我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时,排名只是25%,而我辅修专业的GPA也只有85(相比之下,比政务院同学平均GPA可能还要低两三分)。
- 我没有任何发表,无论在本专业还是在社科的领域。
- 我只是港科的授课型硕士,和我一起被录取的是清华、复旦、牛津的硕士生。
- 在被录取前我没读过任何一本社会学的教材,没听过任何一节社会学的课,甚至我拿到和将要拿到的学位都是工学和理学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我并不敢说我的答案一定是正确的,但我愿意在这里给出我的答案:在我的理解里,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最终录取结果的是你在你选择的subfield的研究潜力,而GPA、发表经历、本硕背景、专业匹配、推荐信等等都只是证明你研究潜力的不同维度。
我所选定的subfield是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这个subfield下最完美的候选人应该同时具有社科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的背景,以及相关的交叉领域研究经历。
这样的人并不很多,这也是我拿到offer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相信我,如果我选择的subfield是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我现在一定在(找)实习。
“利用边际收益”
在我们过去的二十多年的生活中,数字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衡量指标;尤其在学校里,高考分数是一个数字、GPA是一个数字、排名是一个数字,似乎我们参与的生活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游戏。
但是数字只是标量,生活其实是向量。
把向量中某些维度的值从50提升到60的难度,很多时候比把向量中某些维度的值从90提升到91的难度要小得多,但是有些时候前者的收益要更大:最终衡量你的向量的可能是无穷范数,但更可能是二范数、一范数,或者其他什么别的指标。
把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交流能力、其他专业领域内的能力做适当的提升,能获得的边际收益或许会更大。
“做你自己,另外,运气很重要”
其实本科时候是活得很任性的,我是纯粹出于兴趣报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辅修,当初的我压根没指望能从这个辅修当中获得多少“现实”的回报。回顾自己本科的成绩单,除了必修的思政、体育、英语还有一些无关的基础课程,我有30%的学分花在了各种社科类课程上,除此以外,我大概修了30%学分的各种数学课和40%的计算机课程。
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任性”的话,我现在面前的路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收入可能会高不少)。
顺便说一句,我第一次想申请社科的研究型硕士或者博士是在2019年12月,有一次从广外图书馆自习回来的路上还和阔桑说了这个想法,不过我没有付诸实践,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想法在当时都过于离谱了。
上面是“做你自己”的部分,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一路最重要的是运气。
不像很多比较积极的同学,我其实是不太喜欢课后和老师交流的。整个大学我其实就一次在课间去和老师交流,我去问的还不是学术问题,但就是这次交流在九个月后让我获得了RA的机会。
那时候是2019年11月,我收到了港科的硕士offer,当时香港形势一般般,于是我在“香港政府与政治”这门课的课间问夏老师对去香港念书的看法。
夏老师给了我去的建议,在知道了我的专业以后顺便问了我几个计算机技术在一些在做的科研项目上的应用问题,涉及到自然语言处理和图论吧,刚好我都学过,算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
课间也就是十分钟,其实没有说多少东西的。
再下一次就是在期末考的时候我提前交卷(总共我就复习了一个小时,实在是不会做,香港政府与政治这门课我最后应该是考了班里倒数前十),老师认出了我,加了我的微信。
再过了几个月,我成了项目里的研究助理,再然后,在老师朋友的帮助下,我决定申请社科的PhD和MPhil项目。
整个大学的无数个课间我就问过一次问题,但就是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未来生活轨迹。
“平常心,接受可能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我很羡慕那些自信或者盲目自信的同学(尤其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那种),作为一个从小学就开始跑的猪,我见过了无数所谓的超人和学霸:一时瑜亮的朋友去了科大少年班,随后又去Caltech读博;曾经一起集训到最后的同学只用读两年高中;高中不同时期的同桌前桌后桌旁桌先后去了北大……
我想说的是,从我初中一年级见识到人与人的差距能有多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怎么努力过了。
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灰意懒。大狗和小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好了。
就像是高中室友裕达夫说的那样,“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征服一切的浪漫胸怀,而是与自己的生活达成和解的平常心。”
做自己能做的努力,用一颗平常心去迎接可能的结果就好了。
最后的话
说实话这篇文章比我原本想的要长,写的也一般,但是实在是没有力气打磨了,毕竟眼前还是有些deadline的,就这样发出来吧,还请各位斧正(不过我忘记修复博客下的评论功能了,各位可以在朋友圈下作评论)。
祝自己未来几年顺利。
“The man who said ‘I’d rather be lucky than good’ saw deeply into life. People are afraid to face how great a part of life is dependent on luck. It’s scary to think so much is out of one’s control. There are moments in a match when the ball hits the top of the net, and for a split second, it can either go forward or fall back. With a little luck, it goes forward, and you win. Or maybe it doesn’t, and you lose.”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